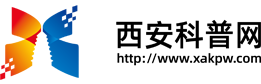人文西安
我国以讲故事为内容的说唱艺术,主要由歌唱和说白交替进行,互相补充,其文学底本的基础为民间叙事诗。经过汉代以来数百年的不断发展,在充分汲取民间音乐和民间文学艺术营养的基础上,唐代的说唱艺术又有了更大的发展,较之前代更加兴盛。长安作为唐王朝的国都,说唱表演自然非常盛行。当时的说唱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,一种是寺院僧尼的说唱,称之为“俗讲”;一种是世俗艺人们的说唱,称之为“说话”。
佛教自传入中国以后,经过佛教信徒们的不断推广,得到了很大的发展。在隋唐时代的长安城,佛教的寺院是非常多的。为了宣传佛教的教义,寺院的僧尼们常借助于说唱这种为民间所喜闻乐道的形式,用来通俗地讲述佛经故事,边讲边唱,这种形式,当时称之为“俗讲”。而俗讲所用的文学底本,就叫做“变文”。据宋代钱易的《南部新书》卷五记载:“长安戏场多集于慈恩,小者在青龙,其次荐福、永寿;尼讲盛于保唐,名德聚之安国。”这里提到的六座寺院分别位于长安城内的晋昌坊、新昌坊、开化坊、永乐坊、平康坊和长乐坊。当时的戏场自是百戏杂陈之所,但既设在寺院之中,俗讲就应占据有利地位。不过,俗讲活动最为兴盛的还不在这四处戏场,而是在保唐寺(尼讲)和安国寺(僧讲)。根据多种资料显示,长安俗讲的兴盛时期应当是在唐代后期,而其中最为有名的俗讲僧就是文溆。据唐代赵璘的《因话录》卷四记载:“有文溆僧者,公为聚众谈说,假托经论,所言无非淫秽鄙亵之事。不逞之徒转相鼓扇扶树,愚夫冶妇乐闻其说,听者填咽寺舍,瞻礼崇奉,呼为和尚。教坊效其音调,以为歌曲。”他所讲唱的内容,虽然仍假托佛教经论,但已更多地掺入了世俗的“淫秽鄙亵之事”,也就是世俗男女情爱之类的故事,所以很受市民百姓的欢迎,并且还激发了乐工们的音乐创作。有一首名叫《文溆子》的曲子,据说就是当时的乐工因受了他讲唱的启发而创作的。由于他的俗讲水平高,吸引人,以至连当时的皇帝都注意到了他。宝历二年(826年)六月,唐敬宗就曾亲临修德坊的兴福寺,“观沙门文溆俗讲”。会昌元年(841年)正月,他又奉唐武宗之命在会昌寺开俗讲。当时在长安入唐求法的日本僧人圆仁称赞说:“城中俗讲,此法师为第一。”也许正是因为俗讲的内容多涉“淫秽鄙亵之事”,所以自唐文宗大和九年(835年)起,朝廷曾一度停止俗讲。直至唐武宗会昌元年(841年)正月,才又重新开讲。此后,又先后于同年九月一日、次年正月一日、五月多次在长安城内寺院开设俗讲,足见当时朝野对这项活动的重视。
在唐代,佛、道二教的斗争是十分激烈的,这也表现在说唱活动中。胡三省曾经说过:“俗讲者……徒以悦俗邀布施而已。”为了广收信徒以募集资财,与佛教寺院进行竞争,当时的道士、女冠们也纷纷模仿俗讲的样子,在道观中讲唱,以招徕听众。韩愈的《华山女》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况,诗中写到:“街东街西讲佛经,撞钟吹螺闹宫廷。广张罪福资诱协,听众狎恰排浮萍。黄衣道士亦讲说,座下寥落如明星。华山女儿家奉道……遂来升座演真诀……扫除众寺人迹绝……观中人满坐观外,后至无地无由听。抽簪脱钏解环佩,堆金叠玉光青荧。”华山女凭借着她的姿色和讲唱,在与佛寺俗讲争夺听众和布施的斗争中,终于取得了暂时的胜利。
除了俗讲之外,唐代长安的世俗说唱、也就是“说话”也是比较盛行的。说话,即讲故事之意。唐代元稹的《元氏长庆集》卷十中就有“又尝于新昌宅说《一枝花》话,自寅至巳犹未毕词也”的记载。按照南宋吴自牧在《梦粱录》中所言:“说话者谓之‘舌辩’,虽有四家数,各有门庭。”灌圃耐得翁的《都城纪胜》、罗烨的《醉翁谈录》等,都有关于说话分类的记载。但由于各书文词含混,近人断句标准不一,因此对“四家”的划分不尽相同,大致包括“小说”“谈经”“讲史书”“说诨话"“合生”“商谜”等形式。然溯本追源,我们就会发现,宋代说话中的“小说”“谈经”“讲史书”等诸种形式,则早在唐代就已经有了。其中演述佛经故事的“谈经”,应当就是唐代的俗讲;只不过唐代的俗讲是由僧尼为之,而宋代的谈经则由世俗的艺人来进行。
小说,就是以讲述各种神仙灵怪、男女情爱、风尘妓女、武侠、公案等传奇故事为主要内容的说唱艺术。此种技艺,唐代即已有之。据唐代段成式的《酉阳杂俎续集》卷四记载:“予太和(827-835)末因弟生日观杂戏,有市人小说,呼‘扁鹊’作‘褊鹊’,字上声。予令座客任道升字正之。市人言:二十年前尝于上都斋会设此。”这表明,小说这种说唱艺术至迟在9世纪初即已出现。听众除了一般市民外,还有一些文人和官僚贵族。而这些文人士大夫除了听说唱艺人的表演之外,他们中有的也擅长此技。唐宪宗时有个叫韦绶的侍读官,就“好谐戏,兼通人间小说”。在我国的文学史上,唐代传奇小说的创作大盛,被收辑到《太平广记》中的很多,它们中恐怕有不少都是唐代小说艺人说唱时所用的文学底本。
讲史书,就是以讲述历史故事为主要内容的说唱艺术。这在唐代也有其踪迹。像唐代诗人李商隐的《骄儿诗》中“或谑张飞胡,或笑邓艾吃”的诗句,所反映的就是当时讲述三国故事的动人场面。而王建的《观蛮妓》中“欲说昭君敛翠蛾,清声委曲怨于歌”的诗句,则又反映了当时艺人说唱王昭君故事的场面。在敦煌莫高窟的藏经洞中,人们就发现了有关王昭君故事的说唱底本《王昭君变文》;此外还有许多其他历史故事的说唱底本,如《季布变文》《汉将王陵变文》《伍子胥变文》《李陵变文》《张义潮变文》等。由这些历史故事说唱底本的大量发现,我们可以看出,讲史书在唐代其实也是比较盛行的;而且,这种说唱技艺与俗讲也有一定的关系,说明俗讲僧尼除了讲唱佛教故事,也讲唱历史故事。只是唐代还未见“讲史书”这种说话形式的名称,想来其内容是包含在俗讲或别的说话形式之中了。
此外,灌圃耐得翁的《都城纪胜》说“合生”为宋人说话一种说唱(说话)技艺。考诸史书,此说似有不确。据(新唐书·武平一传》记载,有次唐中宗在两仪殿设宴,“酒酣,胡人袜子、何懿等唱合生,歌言浅秽……平一上书谏日:‘……伏见胡乐施于声律,本备四夷之数,比来日益流宕,异曲新声,哀思淫溺,始自王公,稍及闾巷,妖伎胡人,街童市子,或言妃主情貌,或列王公名质,咏歌蹈舞,号日合生。’”可见,唐代的合生当源出胡乐,表演时以歌唱为主,穿插舞蹈。抑或还有说,这种以歌舞为主的合生,与其说是一种说唱技艺,倒不如说是一种歌舞戏。 而宋代的所谓“合生”(一作“合笙”),据宋人洪迈的《夷坚志》乙集卷六的记载,是指“指物题咏,应命辄成者”;“其滑稽含玩讽者,谓之‘乔合生’”。也许宋代的合生借鉴了唐代合生以现实生活中的人、物、事为题材以及“滑稽玩讽”的一些特点,但就文献中的记载来看,二者在表演形式上是大不一样的。所以,我们不能因为宋代的合生是说话的一个流派,就认为唐代的合生也是一种说唱技艺。
虽说唐代的合生不属说唱这种技艺,但这并不影响世俗说唱(说话)在当时的流行和受欢迎。据孙棨《北里志序》中说:“其中诸妓多能谈吐,颇有知书言话者。”言话,即说话。为了能多招徕一些客人, 长安城中的许多妓女也熟练地掌握了这门说唱技艺。另据郭湜的《高力士外传》记载,玄宗晚年,退位为太上皇,为了让玄宗高兴,有时也在西内“讲经论义,啭变说话”。啭变说话,当即说唱变文。连皇帝也常听说唱取乐,可见其在当时是很受欢迎的。唐代长安寺院中的戏场以及东、西两市乃至些大街、里坊,常有杂戏演出,说话作为受市人欢迎的杂戏之一,自应列置其间。而其演出时的具体形象,则在西安地区出土的文物中就有生动的表现。1966年,在西安西郊制药厂工地曾出土一组造型生动的唐代红陶说唱俑,系由一个说唱俑和两个伴奏俑组成。说唱俑高23厘米,坐于高凳上,长须,左手扶腿,右手举至胸前,正在兴致勃勃地说唱。身旁的两个伴奏俑均高17厘米,一个盘腿坐于圆形垫子上,双手捧笙认真地在吹奏;另一个两腿交叉侧身而坐,作敲弹状。他们的表情真实而传神,造型生动而逼真,似乎已陶醉在他们的表演之中。此外,在临潼关山唐墓也曾出土六件说唱俑,五男一女,其中还有胡人形象者。这些都为我们了解唐代的说唱艺术提供了具体形象的资料。

西安出土唐代说唱俑
唐代说话的文学底本叫话本,在敦煌卷子写本中就发现有唐代的说话话本《庐山远公话》等。不过,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更多的则是俗讲的文学底本——变文。唐代流行了佛教的变文之后,当时的民间就把变文的名称也用于一般非佛教的说唱。所以,变文的内容除宗教故事外,还有历史传说和民间故事等。我们现今所见的变文,均出自敦煌莫高窟藏经洞,其中大部分为宗教内容,也有一些世俗性的变文,如《王昭君变文》《董永变文》《李陵变文》《张义潮变文》等。而从事变文说唱的,除了僧尼之外,也有一些世俗的民间艺人。如唐代吉师老的《看蜀女转昭君变》诗云:“妖姬未著石榴裙,自道家连锦水溃。檀口解知千载事,清词堪叹九秋文。翠眉颦处楚边月,画卷开时塞外云。说尽绮罗当日恨,昭君传意向文君。”从这首诗我们不难看出,《王昭君变文》在当时就有由俗家女演唱的,而且在表演过程中是有说(“说尽”)有唱(“转”——啭),并且有画卷配合。而从现存的敦煌变文中我们也发现,这些变文多数是散文体的说白和韵文体的唱词(基本上是七字句)相互交织,有说有唱,复沓回环,并在说唱时还辅以观看图画。这种穿插歌唱、图画的形式,常常选择在由白变唱之际。如《降魔变文》中的“且看……若为陈说:(七字句辞)”,“……处,若为:(七字句辞)”;《李陵变文》中的“看……处,若为陈说:(七字句辞)”;《汉将王陵变文》中的“[从此]一辅(即图画一幅)便是变初:(七字句辞)”;《破魔变文》中的“(七字句辞),经题名目唱将来”。这些都是边说边唱并引导观看图画(变相)以加深印象、进一步领会之证。
【我们尊重原创,也注重分享。版权原作者所有,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联系,我们将第一时间删除。分享内容不代表本网观点,仅供参考。】